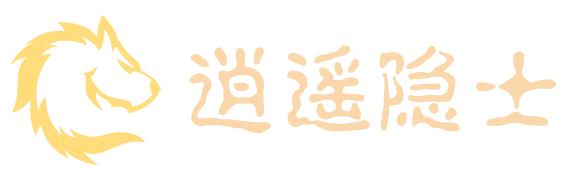老黄是我家的一头牛,它来我家的时候,还是头蹦跳不安的牛犊,那时的我,大约十岁。
一开始,我叫它小黄,因为它通体发黄的皮毛,像十足的赤金,又像在阳光下烁烁闪光的缎子。自从小黄进门,我便多了一项任务,写完作业后去放牛,顺便打一些新鲜的牛草,留给它次日早晨吃。
小黄跟个孩子似的童心未泯,一到了田野里就开始撒欢,我拽也拽不住,索性把缰绳一撒,坐在乡间小路边号啕大哭。小黄忙着啃那些肥嫩多汁的草,很是吝啬对我的同情。
后来,小黄长成了大黄,大黄力气很大,别人家两头牛才能干的活,我们家大黄一个就成。秋收的时候,牛车里装满了金灿灿的玉米,遇到上坡,大黄不用父亲吆喝,老早就会伸长了脖子用力地拉,拉不动了,大黄会跪下来,用膝盖往坡上爬,一寸一寸地把一车粮食拖上去。所以,在整个村子里,大黄的名声很响,因为它能干而自觉,绝不偷奸耍滑。
在乡下,一头牛一旦有了好名声,绝对不是件好事,那些没有牛的农户或是养了一条懒牛的人家,会经常跑来借大黄帮他们干活。只是,我们家大黄,不仅力气大,脾气也大,它没法拒绝自己被借出去义务劳动的命运,但它会以不合作作为抗争。它不允许我们家之外的任何人牵它,它身体又那么壮硕,壮硕到年轻小伙子一看见它发怒都要打憷,没辙。我做惯了老好人的父母,只好在别人来借牛时,把我们家的人也借出去一个,因为没有我家的人,大黄不仅不干活,还会发飙,瞪着名副其实的牛铃大眼盯着人家,虎视眈眈的让人手足无措。
但,大黄的这点劣迹,反倒让我们喜欢它,觉得它是一头有个性的、有宿命感的牛。尤其是大黄在我们家人面前,非常温驯听话。譬如说,黄牛是不肯让人骑的一种动物,只要人骑到它背上,它绝对是要掀屁股仰头地发狂的,不把人从背上甩下来绝不罢休。我们家的大黄就不,我去野地里放牛,偶尔会搞点恶作剧,比如说想爬到它背上去。因为大黄身材高大,我想爬上去很困难,就会把大黄牵到一棵树旁边,我往树上爬几尺,从树上跳到大黄背上,当然,不是骑,是趴在它背上,为了见势不妙就快速溜下来。
每当我跳到它背上,大黄的身子就会一颤,它抬起头,看我几眼,继续吃它的草。那会儿,趴在大黄背上的我很骄傲,因为我破掉了黄牛不能骑的传说。等远远地看见村子里炊烟袅袅了,我会把装满青草的篮子,放在大黄背上,扶着它不掉下来就成了,能省掉不少力气,认识家的大黄就会慢悠悠地带着我和它的早饭回家。
渐渐地,父亲的鬓角开始有了白发,我也长大了,大黄也变成了老黄。它变成老黄之后,依然威武不减。乡下的生活条件也渐渐地好了,各家各户开始添置了机械农具,需要老黄干的活越来越少了,大多时候,它站在院子里,悠闲地反刍,看着家里的人进进出出。
因为没有牛可以干的活了,所以,村子里养牛的人家也越来越少了,也有不少人动父亲把老黄卖了,父亲不肯,他舍不得,我们也合不得,说老黄给我们家出了一辈子力,我们给它养老算了。
可是,后来发生了一件事,迫使父亲不得不打起了卖掉老黄的主意。舅母得了淋巴癌,花空了舅舅家所有的积蓄还借下不少外债,舅舅再也借不到钱了,可舅母的病还是要治的。舅舅来家找母亲商量,那是个夏夜的黄昏,父亲和舅舅坐在院子里抽烟,他们时不时地看一眼老黄,老黄在橘色的霞光里安然反刍。
我不知道舅舅跟父亲说了什么,只知道那天晚上母亲给老黄的晚饭里加了很多好料,然后摸着老黄的头,掉眼泪。
第二天,老黄就被牵到集上去卖了。卖掉老黄的那天,父亲和母亲都没说话,也没吃饭,父亲只是把一沓钱拿出来,递给母亲,让她抽时间给舅舅送到医院去。可是,还没等母亲把钱送给舅舅,老黄就回来了,是被买家送回来的,因为老黄到了新家后不吃东西,一连三顿,不吃不喝,新主人急了,以为老黄有病,次日上午就给送了回来。
乡里人是重信誉口碑的,把一头病牛卖给别人是件令人不齿的事,父亲退了钱,收下了老黄。可是,老黄一进我们家的牛棚,立马就大快朵颐。
因为舅母的病,老黄并不能因为恋旧而逃掉被卖的命运,父亲调养了老黄几天,又把它牵到了集市上……
父亲一连卖了它三次,它三次都被送了回来,就是一个原因,老黄到了别人家就不吃不喝,一被送回来,它就什么毛病都没了。三次被卖、三次到了别人家不吃东西,又感念着它的好,父母实在是不忍心再卖老黄了,决定另想办法帮舅母筹住院费。
或许是因为父亲卖了三次老黄没卖掉,在乡里,多少也有点传奇色彩,没过多久,有人找到家里,说自己是养牛高手,想买我们家的老黄。而父亲四处帮着舅舅筹集舅母的住院费并不顺利,见那人说得如此恳切,踌躇再三,答应了。
当然,买牛的人把价钱压得很低,因为他知道我们家正等钱用,而且他发誓自己的养牛手段多么高明,绝对不会像前三个买家一样,因为老黄不吃东西给送回来。
那人牵走老黄的第二天,就有人跑来告诉父亲,那人不是什么养牛高手,而是个牛贩子,专门为屠宰场收牛的,父亲一听就急了,因为父亲卖老黄的前提必须是买回家养着而不是送到屠宰场。
父亲骑上单车就往那人十几里外的家奔去,想把老黄从屠刀底下救出来。
可是,父亲还是去得晚了。那人在这天早晨就把老黄送到了屠宰场,父亲一路追着往屠宰场去,快到屠宰场时,父亲听到了一声枪响,是猎枪。父亲的心一沉,自行车就歪进了路边的沟里。
父亲的腿骨折了。
后来,父亲说他和老黄有心灵感应了,觉得那一声枪响得不平常,果然是,老黄走了。
牛贩子牵着老黄到了屠宰场门口,老黄闻到了同类的血腥味,就发了飙,挣开了牛贩子沿着马路往回狂奔,牛贩子招呼着屠宰场的人追出来,用猎枪射杀了老黄。
我们的老黄没了,卖它的钱,也没能救舅母的命,没过两个月,她也走了。
后来,我们很少提起老黄,因为一提起它,无言的内疚就会攥住我们的心。虽然我们不说老黄,但它,一直是在的,在我们心底的某个角落里,它安静地反刍。在我的想象里,它安详的眼里,有一种说不出的悲伤,那种任劳任怨后却不能自主命运的悲伤。